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会注意到这些项目的缓慢和渐进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也许,生活中最有趣的时期之一建筑师就像我自己经历了黎巴嫩革命,重塑了我对城市景观的理解,我从小就习惯了城市景观。
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建筑师和投资者看到他们的项目变成了充满活力的新庇护所,代表了公众作为一个新的城市结构的建筑师。
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误解之一建筑学——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城市规划——是它们在预期用途方面的静态寿命。我们看到城市和结构作为经过仔细规划的长期决定,以确保其最终地位。果断、不可逆转、刚毅.
这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冲击,对建筑师来说,是一种职业冲击地标性建筑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变化。一想到一个精心规划的项目或一个有条不紊的城市可以完全无视建筑师的所有预测和辛勤工作——在相当字面意义上的48小时跨度内——是令人着迷的。它推动了这种感觉,即我们只是技术人员。建筑师和空间、体验和品质的决定因素是人。我见过一场“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武断的概念,精心重新设计了整个城市。它成为了自己的建筑运动,促使我问自己一个问题,革命的架构是什么?
建筑革命是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利用

也许我的童年的一大亮点是听所有的故事传统市场填补的空间回贝鲁特市中心的60年代,一个壮举,我这一代没有经验,内战后,立即导致的过度私有化和商业化贝鲁特的核心。这个故事对世界上许多地方来说并不陌生,在这些地方,城市结构的本质慢慢地,但肯定地,私有化了,直到文化的光环消失在浮华的摩天大楼、保安和价格过高的咖啡的海洋中。传奇的殉道者广场——几乎不再是一个“广场”了——周围是高速公路、停车场和商业办公室。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建筑师来说,最美丽的景点之一就是200万人重现了我们行业的前辈们几十年前努力奋斗的城市愿景。非法私有化的海岸曾经是公众的空间,如今数百人带着他们的传统早餐来到这里,坐在“Zaitunay Bay”的人行道上,以示对文化的蔑视。曾经只能从长辈们的故事中听到的传统市场,在市中心封闭的街道上重新建立起来。各个阶层和教派的人们搭起帐篷,手拉手,展开讨论和社会活动,重新创造了这个曾经私有化的国家地标的城市梦想。沙发和床被搬到“指环”桥,在Airbnb上被列为抗议者的免费户外住宿空间。这场革命成为连接我们与过去和我们的城市肌理的纽带,比迄今为止任何建筑师都做得好。
有没有计划到看似有机然而令人震惊的即时转化,其中人们只是知道在哪里的功能被划分。他们意识到烈士广场是为娱乐和里亚德埃尔Solh广场是为严重抗议。他们知道在哪里建立市场,以及如何将讨论区分开。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安东尼·阿塔拉反映了这个最好的,在革命年代市中心的他更新的网站的计划,显示了城市的重建,以及公民强制的城市结构。

革命的建筑是国家地标的开垦

户外并不是被人们重新利用的唯一空间,他们确保恢复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建筑地标,这些建筑曾一度面临被各自的主人拆除的威胁。也没有多少人能说自己看到建筑以一种如此迷人的方式转变,使一个废弃的、被破坏的肮脏的混凝土结构重新变成全新的、外来的功能。

也许建筑师约瑟夫·菲利普·卡拉姆不可能预见到这座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建筑的命运,”圆顶城中心作为黎巴嫩第一家电影的悲剧故事,它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中被彻底摧毁。但它会进一步让他震惊看到这毁了复兴成为抗议者的交汇点,讨论和讲座中心,利用电影的旧椅子,和一个夜总会的音乐扭动neon-covered顶层,同时仍然尊重地位电影院,举办免费电影放映在它的废墟。最重要的是,随着外部楼梯的增加,建筑的蛋形屋顶成为了革命新城市景观的最佳视角。在此之前,The Egg还举办了一场变装秀,作为Saint Hoax艺术展览的一部分。

这推动了我们建筑的进化本质,而这一本质永远无法预测人们对建筑的使用。我们创造了外壳——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蛋形外壳——但建筑师是最后一个决定其内衍生活动的人。

其他回收的地标包括奥斯曼帝国风格的“大剧院”和标志性的烈士雕像。
革命的建筑具有无限的想象力

作为建筑师,我们已经被教育了无数年,形式是如何遵循功能的,但他们很少告诉我们想象力是无限的,或者建筑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通过非建筑师的眼睛去看我们的作品(甚至是自然的作品)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不受传统的限制。
一场革命让你以非建筑师的视角看待空间,当我们构建这些空间时,社会帮助激发它们。一个例子就是伟大的城市的黎波里,它曾经是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痴迷之地,并被提议为未来之城。的黎波里的光明广场(Al-Nour Square)在重新想象中没有休息。有一天,它变成了中国最大的锐舞派对,在网上疯传。另一方面,市场的建立给了它新的生命。残疾人受到欢迎,他们可以居住的空间,而中心雕塑成为一个指南针,创造了新的运动轴。
另一方面,Jal-El Dib的天桥允许两层的抗议集会,上层作为视觉和记录的有利位置。最后,泰尔的抗议延伸到水域,以船为中心的集会创造了公共海滩的自然延伸。
一个革命的结构是包容

最感人的壮举之一的一场革命,也是每一个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应该骄傲的,是建立社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一个不可逆转的程度,一个贫民窟使富人和穷人在当代塔,女性对我们的讲台和阶段,还有男人来我们精致的艺术画廊。学校和养老院手拉手,教堂和清真寺人满为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们经常认为我们的项目所针对的社区是排外的,然而只有目光短浅的建筑师才会对无意的社区以新的方式占据这些空间的概念感到厌烦。
一场革命的建筑是对建筑师错误的高度评判

这就是,建筑责任制。这是建筑师经常遇到的问题。谁让你为你的失败负责?mis-considerations吗?是投资者,还是占领者,还是政府?
这场革命告诉我,公众,就像一个实体的抽象,对建筑有着非常强烈的看法。否则,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会选择公开破坏5亿多美元的项目,同时愉快地占领一个几乎被摧毁的国家地标?为什么要放弃那些经过翻新、高质量的空间和建筑,而去拥抱那些不那么方便、但更感性的选择呢?

也许这场革命展示了我所见过的建筑责任制的第一个实例。人们抗议针对我们城市结构的犯罪行为。他们避开并摧毁了那些摧毁了文化和历史地标的建筑——甚至是矗立在现在已经失去了巨大价值的废墟之上的建筑,为那些试图相互争夺关注的后现代主义立面下的投资腾出空间。他们抗议那些禁止我们进入公共空间的建筑。这种建筑不尊重我们的地标,忽视了我们的本质。破坏了我们生物多样性的建筑。建筑覆盖了我们的海岸景观,并占据了我们的公共海滩。这场革命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人们密切关注着建筑师的道德指南针。
虽然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真空项目,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贝鲁特梯田被认为是极度不满的,因为它接受了进一步的城市化,并限制了一个曾经是公共财产的区域,在一个由窃取公共土地的投资者组成的委员会。
因此,革命的架构是能够经受住责任考验的架构。
革命的架构把距离连接起来,把邻接的东西断开

曾经是竞争对手的社区,几乎完全脱离了宏观城市的规模,却成功地超越了空间,打破了障碍,把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人民连接起来,从国家最高的北部到最低的南部。超过10万人的手拉着手的人链覆盖了整个海岸。交通倡议已经看到社区和集中地区在团结行动中走向新的未知领域。公共汽车将抗议者沿海岸运送(从的黎波里到纳巴提耶的团结信息),与此同时,其他道路被封锁,以指定特定区域供公众、无歧视的行人进入。
抗议者并不是这种变化的唯一催化剂,内部安全部队设置了安全路障,并限制进入特定区域,进一步改变了我们曾经习惯的联系。因此,不仅城市本身的城市结构发生了变化,整个国家的宏观城市分布也发生了变化。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这种有机改造最有趣的地方,应该是它的活力本质,根据不断发展的需求,一天又一天地转变和变化。这就创造了一些短暂的城市,这些城市在孕育着革命的故事。
革命的建筑有更生动的外观


废弃的野兽派立面冰冷肮脏的混凝土在贝鲁特的Egg中被赋予了色彩。的黎波里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被爱国信息所覆盖,就像在的黎波里的光明广场上看到的那样。扩建部分被添加,其他部分被销毁。艺术和建筑融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实体,重新创造了城市褪色的调色板。
在某种程度上,一场革命的架构是可持续的

为了总结这场建筑革命的教训,我们最后简要地(但令人惊讶地)考虑到用户自创的可持续性,而人们在没有资金或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设法寻找令人印象深刻的可持续性倡议。从回收计划到在街道和建筑上增加植被,再到对濒危建筑活载能力的全面研究,这些研究允许抗议者自发地对这些建筑内的游客配额进行监管,这些倡议表明了非建筑师与我们分享的对可持续性的关心。
这段经历可以和我在大学里学习的理论和实践课程一样有价值,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因为它帮助我把它看作是我们生活中更有活力和活力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以前认为的。一场革命的架构是一场变革,是一场出乎意料的曲折,这与我们往往做出的非常复杂的规划背道而驰。它破坏了我们的想法,却对我们梦想在这些想法下创建的社会具有建设性。这是一个教训,作为建筑师,我们需要积极倾听周围人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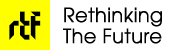











1评论
我发现这非常有趣,因为它把我上周的一些想法变成了文字。就在上周,我还在想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鸡蛋的存在。当我从革命的角度看待它时,我注意到我的脑海中有它,但我从未主动承认它。这场革命让我积极地对这些被忽视了很长时间的建筑进行分类,尽管它们在建筑上很重要